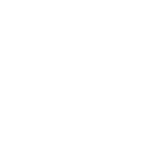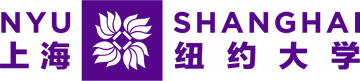2003年6月,严登峰从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毕业,在刚刚创刊的《东方早报》开始了第一份工作。
初到上海,他被分到“法律条线”,成了这座城市里,最早跑庭审现场的政法新闻记者之一。
“上海一中院下辖的法院,我基本都跑遍了。”当时身旁坐着的,多是像他一样的年轻人,大家一起边听边学。
原以为记者只是“写文章”,入行后才懂得,真功夫落在下笔之前——于混沌信息中理清脉络,在一次次闭门羹后坚持追问。这份工作对训练、经验和判断力的要求远超想象,“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优秀的同行。”
一年后,他认真考虑起转行。面前的路有两条:一是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,为此,他买回厚厚一摞材料,准备司法考试;二是拾起大学时就产生的那份对市场营销的浓厚兴趣。
21世纪初的那些年,营销与品牌的理念正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,从商业延展至公共议题,“国家营销”“城市品牌”等概念,也兴起了。
2005年,他离开上海,去香港浸会大学读市场营销学硕士,后来又到香港科技大学读博。
2012年博士毕业,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(UTSA)向他递来橄榄枝。犹豫时,导师一句“趁年轻,多去看看”,轻轻推了他一把。
在美国六年,他从助理教授升至长聘副教授,生活渐稳。而每次回国,他都像撞进一个加速的世界:纸质菜单变平板点菜,平板又化作桌角的二维码,其间相隔,可能不过半年。
近距离观察新颖的市场营销实践,知道领域内正在发生什么,对他而言,很重要。
2018年,严登峰决定回国,加入上海纽约大学。
反复思量的日子里,一段冬日的记忆闪回。2007年12月,他刚读博一,第一次坐在“学术冬令营”会场的台下。当天受邀分享的嘉宾里,有后来出任上海纽约大学商学部主任的陈宇新教授。
面试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进行。收到offer那天,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约,甚至没先去未来办公的地方看一眼。
时隔15年,严登峰回到上海。
当时,上海纽约大学还在世纪大道,他的办公室正对着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大楼。一抬眼,便能望见楼顶那座熟悉的报时钟。曾经跑新闻的地方,如今与他一窗之隔,命运神奇。
政治学、政法记者、市场营销、大学教授,几番专业和职业变换,让他对“路径依赖”、人生规划有了新的理解。“人在每个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,都有一个适应新角色的过程。许多能力,其实都可以在过程里慢慢学会。”
“曾经认定绝不会喜欢的很多事,真去做了,会发现未必如此。”人不必被初始轨迹限定。真正的节奏,是在随缘中守住专注。
“教学新人”的进阶
“20年前,如果有人问我喜不喜欢教书,我肯定说不喜欢。”
那时的他,认为自己“是个i人”,一心只想埋头做学术、写论文。可命运偏偏把他推到了需要“不停说话”的位置——读研期间,他成了一名助教。
刚开始用英文和学生交流,他说得磕磕绊绊,表达“支离破碎”。期末的教学评估,自然拿不到高分。
读博后,他第一次站上讲台,独自面对本科生,讲授“消费者行为”(Consumer Behavior)。

有段日子,他常在网上观摩名师公开课,一边感叹“怎么会有人讲得这么好”,一边琢磨如何用到自己的课上。
“教师既是导演,又是编剧,同时还是演员。”他说,“一节课就像一集剧,哪里该设问、哪里该展开难点、哪里又该轻松一下,都要设计。如果是持续一学期的课,那就得排成‘连续剧’,多少集、每集讲什么,心里要有数;如果只是一天的短期课,那就得浓缩成一部‘电影’。”
“而且每学期,学生都会换一批,你得尽快了解他们。”
即便是现在,每学期上第一堂课前,他还是会紧张,“和学生熟悉了,才会慢慢放松。”得益于小班教学,一堂课通常十几人,“基本上两三周下来,我就能记住每个人。今天谁没来,看一眼就知道了。”
为了让学生保持兴趣,就算同一门课教了多年,他每学期仍会花大量时间修改教案。“现在一节课往往三小时,我理想的状态是全程无‘尿点’,做到这点并不容易。”
“找出那些就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例子,可能是我备课中最花心思的部分。”
从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的实施,讲到市场营销对公共政策的影响;从营养成分表上的千焦和人们惯常使用的卡路里,引出标签对消费者的潜在影响;就连学校咖啡馆的“买九送一”集章卡,也被他设计成了课上的小组作业。
“身边的同事、同行都非常乐于分享资源。他们经常带学生走进企业,亲眼看到营销决策是如何在现实中制定的。这种近距离的观察,对学习的帮助是无可替代的。”
学生看到了“所学即所用”,他也在每一次的教学迭代中不断积累。“当你能在一个领域长期探索、观察,对问题的理解会越来越深,自己的竞争力也会随着时间增强。这本身就让人感到踏实,也让人喜欢。”
2024年12月,严登峰荣获当年度“宝钢优秀教师奖”,成为上纽大首位获此殊荣的教授。
得知消息时,他有些感慨。不知从何时起,教学已不再只是一份工作,而成了一件让他愿意全心投入的事。
“谁能想到,当年那个评分很低的助教,现在也能站在这里领教学奖了。”
当营销学拥抱“人”的全部
在市场营销的科研版图里,严登峰始终耕耘在“消费者行为”这一方向。人的心理,是他从读博到现在开展研究的基础。
“一天还是二十四小时,人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因为科技进步而突飞猛进。”他说,“千百年来,心理底层的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。”因此,他的理论框架也相对稳定,让他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浪潮中,得以保持清晰的着力点。
现实中的决策,往往不像经济学假设的那般绝对理性。照理说,相同的信息该导向相同的选择,可事实却是,酒瓶上标注“二十年陈酿”还是“产自2005年”,都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。
这类决策中的“偏差”(bias),一直是他的关注点。也正是那些因人而异、难以精准预测的部分,让他觉得市场营销充满魅力。
价签、宣传栏、广告牌……生活中,他会下意识地留意上面的数字和文案,揣摩不同人看见它们的心理活动。
2019年,他围绕“数字信息如何影响消费决策”的研究,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”。此外,他还先后入选了上海市“曙光学者计划”和MSI Scholar。MSI Scholar由美国营销科学机构(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,MSI)设立,旨在表彰市场营销领域表现杰出的中期(mid-career)学术研究人员,那一年,全球仅30余人获此荣誉。
与20年前相比,“营销”已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,甚至因为时常和“贩卖焦虑”等联系在一起,还蒙上了一层贬义的色彩。然而在他看来,营销依然大有可为——尤其是在健康与福祉这类真正重要的议题上。
比如,过去30年,我国居民膳食中脂肪的比例持续攀升,这背后潜藏着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隐忧;又如我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,长期远低于很多国家和地区。
如果说,营销擅长的是把一个行为做成习惯,那么更值得被推动的,恰恰是那些科学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“希望有一天,天气一冷,人们能像想起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’那样自然地想到:是时候去接种流感疫苗了。”
无论是让人关注、读懂食品成分表,还是促使企业进行更负责任的传播,他希望通过研究,推动哪怕一点积极的改变。
2021年夏天,他走进浦东图书馆的报告厅,参加由上纽大图书馆与浦图合办的“阅读与人生”系列讲座。台下坐着十岁的孩童,也有八十岁的长者。
那是一场围绕“数据素养”(data literacy)的分享。他没有使用晦涩的术语,而是聚焦最实用的方法:怎么追溯信息的源头,如何通过交叉比对辨别内容的真伪。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,这些技巧,每个人都用得上。
“营销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观念,帮助大家做出更健康的选择。”当亿万次微小的选择汇聚起来,改变的将不止是市场。
在快时代,做一名“慢学者”
为什么薯片通常是圆的,玉米片却是三角形?
带着从日常中萌生的问题,严登峰初到上纽大时,就开始了对“形状语言”的研究。他和团队投入了近七年时间,探究我们习以为常的设计背后,是否藏着影响消费选择的规律。
最初,他们委托企业设计出不同形状的包装——正梯形、倒梯形、对称与不对称的,邀请参与者仅凭视觉估算重量。
结果发现,形状确实会改变人们对“量”的感知。当包装在视觉上显得更“稳”,比如底部更宽、结构对称、重心居中时,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它更“重”。
这种视觉上的“重量感”,进一步影响着人们对食品价值的判断。在消费者心中,“重”常与“真材实料”“热量高”联系在一起。因此,对零食这类“享乐型”(indulgent)产品来说,“显重”的包装能提升购买意愿;但对标榜“轻盈”“健康”的产品,同样的“显重”可能被理解为“负担感强”“不够纯粹”,反而降低了吸引力。
历时多轮的审稿与修改,研究也不断深化。其间,他们通过在电商平台抓取酸奶的数据进行验证,并将实验扩展到巧克力、瓶装果汁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,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测试,确保结论不限于特定情境。
2025年7月,这项始于2018年的研究,最终发表在《市场营销研究杂志》(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)。“从启动到刊出,往往需要四五年。更多的论文甚至走不到最后。”他说,“这个过程,最需要的是耐心。”
而在他看来,需要耐心的,远不止发一篇论文。
“我希望通过研究,推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,这当中也包括我自己。”他的生活如今很是规律:每天早上送完孩子上学,七点半不到,他会先去学校健身房。“每周坚持练一练,饮食上稍加留意。锻炼的效果可能需要三个月、一年,甚至更久才会慢慢显现。”
这种“日拱一卒”的坚持,是他从研究和生活中悟出的道理。“我相信,好的事物都需要时间。”
“社交媒体上有太多的‘速成神话’,要么真假难辨,要么是极小概率事件。就像种树,长得太快的,根系往往都浅,一场风雨可能就倒了。”他和学生分享,“真正的成长,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。如果你追求的是深厚、不可替代的竞争力,那就必须积累别人没有的东西:独特的视角、经年累月的洞察。这些,都无法速成。”
简历可以堆砌经历,但内行人的一个问题,就能探知深浅。而时间,终会为那些持续深耕的人,赋予一份扎实而沉稳的礼物。